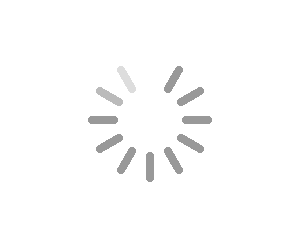小姑娘无辜地看着我,似显无奈。我鼓励她再大点声,半晌后她终于大声说了一遍,声音很嘹亮,此刻全班也都为她鼓掌,伴随着有节奏地掌声,她轻轻地笑了。我有些愣,呆呆地看着这五十来个有黝黑的皮肤,两腮有高原红的孩子们,心底涌起了一种暖洋洋的成就感。
接下来孩子们越来越活跃,手伸得老高,有的已经不知不觉地站了起来,要回答问题的孩子们一遍遍扯着嗓子喊“老师,老师”,恨不得把手伸到我鼻尖。直到下课竟还有十来个孩子想说但没来得及,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。
下了课,孩子们又拿着课本要我签名,孩子们围得太紧,外面的孩子们挤不进来,站到桌子上,“呼啦”一下子把书从上面扔下来说:“要写姓名,电话,QQ号……”
这帮孩子,竟然还知道QQ!
我说,我把电话写在黑板上,你们自己抄。一个男孩蹭到我跟前,一脸“霸道总裁”的架势对我笑着说:“就要你写!”我拗不过他,只得给他写了,别的孩子又不干了,书又从天而降……
(四)
从楼里出来,正好碰见宋老师去她教过的班,宋老师让我跟她一起去,说孩子们要给她
表演节目。一进班,同学们“哄”得炸开了锅,他们已经把桌子往后拉了。班长是主持人,节目有唱歌、有跳舞,还有三个男孩表演赵本山的小品。
十几分钟的表演,他们没瞥过一眼书稿,流流利利,一颦一笑都学得有模有样。那天晚上,我们挤在沙发上看电视,我和田田缠着宋老师让她讲家访的事。宋老师把书包放下,捋捋头发,开始讲起:“我去的那家在牧区,家里四口人,孩子、爸爸、妈妈和爷爷。妈妈是个聋子,爷爷前两年不小心摔了一跤,因为没钱治,就那么拖着。”
她拧开水瓶喝了口水接着说:“家里进门就是床,旁边有个小柜子,还有一个很矮的类似于
茶几的小桌子,平常孩子就趴在那个桌子上写作业。家里没有一个电器,我都不知道他们今
天晚上吃什么。”我问宋老师:“那他们家谁挣钱呀?”
“就是孩子的爸爸呗,孩子的爸爸给人牧羊,一般在外面。”宋老师顿了顿接着说,“等于
平时就儿媳妇和爷爷在家,孩子去上学了嘛,爸爸在外面放羊。”
“那他们怎么交流啊?”
“是不是能用手交流一下啊,我估计他们就能不交流就不交流了吧!我刚进门时爷爷就坐在窗子旁一个小板凳上,一点一点往前蹭着走”
我脑子里浮现出一幅画面:爷爷拖着一条腿坐在板凳上,妈妈坐在床边,两人都不说话,呆呆地干自己的事,屋里昏暗昏暗的。
“唉!”连田田都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第二天我去李校长介绍的两个孩子家,我想资助他们,妈妈提的要求是孩子学习还可以但家长要善解人意。两个孩子三年级,女孩回族,叫马兰梅,妈妈说因为当时是斋月就不请我们去家里了,只是去操场聊了聊。在一起也没座太多时间,女孩很腼腆,几乎没说给一句话。她妈妈介绍说,家里三个姑娘,老大六年级刚毕业,叫马兰花,老二五年级,叫马兰香,马兰梅是老三。老大和老三都很腼腆,老二挺爱说话。
接下来去的男孩家就是汉民,男孩叫朱文臣,家离学校不远,走读。他爸爸是司机,妈妈在宾馆工作。本来班主任说,家里就奶奶在,但后来妈妈也请假回来了。文臣的妈妈和奶奶很热情,进家就给我们到奶茶,还拿邻居送的馓子给我们吃。家里租的是平房,十几平方米大,被柜子床桌子灶台挤得满满的,条件应该比宋老师去的那家好一些。起初我们坐在家里,文臣自己去门口的空地玩了,我不想吃东西,但又盛情难却,就出去找文臣。
文臣正拿着个塑料盘子对着墙打乒乓球,我过来他让我也试试,我试了两下后想起手机里有前两天和同学去动物园玩时照的照片,我想祁连大概没有动物园,就给他看照片。边看我问他:“你去过动物园吗?”
他摇摇头。
“你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儿呀?”
“西宁。”
“你去干嘛呀?”
“治病。”
我一愣:“治什么病?”
“肺结核。”
我对肺结核没什么概念,就是想起以前语文老师讲鲁迅就是因为的肺结核去世的,但好像这个病现在能治好。我想想我游山玩水去过的地方,又想想北京的热闹和那么多景点,我突然想把我知道的所有关于这些动物的东西都告诉他:什么海豚很聪明,长得像鱼但它是哺乳动物;杀人蟹很大,广身子就有你的头那么大;海马是由爸爸抚养孩子;火烈鸟全身是红色的,有的时候它们单脚站着;袋鼠平常跳着走路,袋鼠妈妈的胸前有一个口袋,小袋鼠出生后就爬到口袋里生活,它们生活在澳洲……
“你知道澳大利亚在哪儿吗?”我突然问他。
他摇摇头。
“在,呃——你到太平洋在哪吗?”
他还摇摇头。
“你见多地图吗?世界地图?”
他没回答。
我猛然意识到,这些孩子们最需要的不是更好的生活学习环境,或是多么优秀的老师,而是一个机会,去了解雪山油菜花青稞草外面的世界,去了解那些我们早在幼儿园就已经烂熟于心但他们闻所未闻的“故事”!
我一直不停地给他讲那些“故事”,直到被妈妈催促着离去。
临走那天晚上,正好是寄宿生返校,宋老师去家访过的女孩张雪莲给宋老师打电话,想再见一次宋老师。我们去食堂吃饭的路上路过宿舍楼,几个孩子趴在窗台上,怕错过宋老师,宋老师看见了在楼下喊:“张雪莲!”上面的孩子一下没了影,几秒种后雪莲和她同宿舍的三个孩子气喘吁吁地跑下来,送了宋老师一叠自己画的画,最上面放着几朵明黄色的油菜花。
吃完饭,宋老师答应去宿舍里找她们。走进屋,宋老师问雪莲:“哎雪莲,我去你家的那天你们晚上吃的是什么呀?”
“馍馍啊!”
“只有馍馍吗?”
“嗯,还有茶。”
宋老师没再说什么,便给她们检查作业。宿舍里孩子们说屋里雪莲成绩最好,大概班中十几名。班里五十几个孩子,十几名应当还不错。
作业里主要是周长面积的题,还有一些列方程的行程问题。宋老师一道一道的看,主要看思路,计算一般没给检查。孩子周长面积分不清,列的方程基本都错,很多题明显题意没理解;整套练习看下来错的远比对得多。
我心里感觉怪怪的,我说不清这意味着什么。桌上倒扣着一本很旧的历史故事书,泛黄的纸被折了脚,已经掉页。
(五)
那天下午回来我和田田去找宋老师祖老师玩。在宾馆里,我们挤在她们的床上,电视上播着87版的红楼梦,电视前宋老师的手机一亮一亮。宋老师打开看,有好几个陌生号码的未接电话,宋老师问他们是哪位,那边回是二完小的学生,要请宋老师出去看电影。宋老师说待会要开会,晚上要去卓尔山,今天不行,下次吧。孩子问几点回来,宋老师说不知道,那边回:“反正今天就要请!”

孩子们在挖野菜作者供图
祖老师总逗田田,说要把宋老师埋到油菜花地里,来年收获一百个宋老师。每次田田都一乐一乐的,被宋老师听见,起初说他们校长要乐坏了,后来改口说,她老公要乐坏了,一下子来了这么多老婆。逗得田田咯咯咯的笑。
我从小手容易冰凉,祁连早上挺冷,我的手更是冰冰的。早上去学校的路上,宋老师给我捂手,气我说:“手脚冰凉的人没人疼!”
我低头看看被包在她的手里的我的手,到嘴边的话是:“你不就疼我吗!”可是话到嘴边还是咽了下去,宋老师一点都不怕痒,还特会挠人,我就说:“不怕痒的人才没人疼!”
“切!”
“哼!”
宋老师性子急,我性子更急,每次都是我和宋老师远远地走在前头,祖老师拉着田田喊:“喂,你们等等脚小的!”
宋老师不理,我笑,迎面走来几个学生,手在头顶上一挥:“老师好!”
宋老师扭过头眨眨眼睛来对我笑。
电视的节目已经换到《精忠岳飞》,旁边田田一个劲问祖老师韩世忠的妻子是怎么死的,祖老师一遍一遍地讲……
当时我心想,难怪学生们要缠着这帮老师!
我回来后一天,文臣拿他妈妈的手机给我发短信,问我什么时候再去。我说,至少得等到明年暑假,我也要上学呀!几分钟后,文臣回:我等着。
我用我贫乏的语言真实并尽可能细致地描写出我看到的祁连,一路匆匆,我看到的只是这些孩子每天平淡的生活中的一个侧面。
我们只在这个学校呆了四天。祖老师以前去密云支教过一年,她说当地很多孩子来上学就是因为家长觉得少一人的饭钱,并非来学什么知识。她老说:“支教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。”我问:“我们想象的支教是什么样,真实的又是什么样?”祖老师不答。我想,有些东西,看到了和感觉到了是两码事。
(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高一(3)班丁思勤)
文章来源于:http://xiaoxue.ljyz.com.cn 小学网
网站内容来源于网络,其真实性与本站无关,请网友慎重判断